(按:《广东美术史》是研究广东地方美术的重要著作,出版于1993年,研究对象的时间下限为清末,该书对研究广东美术通史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引言”部分。)
本书将要论述的是广东美术的发展过程,从性质而言,它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美术通史。就这个框架本身,有些问题是应该提出来讨论的。另外,在完成本书的基本部分之后来撰写这篇引言,有一些在写作中一直萦绕于心头的问题,以及伴随着写作而产生的对于这段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钱穆先生语),都是我迫不及待地希望能首先呈献于读者的。
一
迄今为止,国内美术史论著的撰写格局基本上仍是分为通史、断代史、门类史、个人史四大框架。地方史性质的著作容或有之,但总以某种地方门类或某个地方流派为研究对象,实则是一种局部的专题性研究。
在史学领域中,地区通史在各地已续有出现。在美术史研究中,地方美术通史似未见有,——但愿这只是笔者的寡闻。
中国的确是地大物博,每一地方的美术史迹、史料,除了有幸能入选上述四大框架之外,剩下的还是浩如烟海。这些文化史迹的最好命运,似乎只能是等待某项专题研究的垂青。
当然,在实际中,它们已经有充分的机会在考古学和地方文物志这两大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时它们是“被利用的”,其美术的性质基本上被撇于一边,更遑论整合为地区性的美术通史。
地区美术通史的必要性并非仅是服务于地方文化史研究。从专业史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完成一部完整的全国性通史的重要条件。缺少这个,似乎难以期待任何全国性的通史能具有极度丰富与生动的特性,会恰如历史本身曾经有过的那样。
当然,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仅在于它们可以为全国通史提供丰富的、新的入选材料——事实上由于篇幅所限(尽管可能是十几卷的特大部头),几乎不可能有一部全国式通史在每一阶段的论述上都容纳进所有有价值的地方史料,而在于对它们进行系统研究的结果,有可能导致全国性通史研究中的某些变化,比如,变换角度、重新确立遴选的标准、深化在价值判断上的认识,等等。
由于缺少地区性美术通史的研究,“全国”这个概念便总有些问题令人不能放心,比如,在它名下的其实只是某些地区的情况——它们是经过遴选而成为“全国”的,而之所以会让它们入选,往往是因为它们符合某些理念,如“时代风格”等。
在这方面,谭其骧先生以其专业的敏锐与文化史的卓识而使我们获益良多。他指出,“不能把整个王朝疆域看成是一个相同的文化区”。“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他的研究表明,没有什么“全国文化”,只有地区文化;没有什么“时代文化”,只有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因此,他认为所谓“中国文化”应该是在两个意义上进行把握:第一,“理应包括所有历史时期中国各族的文化”,第二,“中国文化”的共同点就是兼容共存。(《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载复旦大学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我们是否有勇气思考: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 没有什么“中国美术史”,只有地区美术史;没有什么“唐代美术”,只有唐代各地区的美术?
在任何文化史的研究中,区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由于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喜欢强调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在表述方式上,我们偏爱于笼统的而不是具体的;在文化的单位上,我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强调大一统,自古以来就是大一统,讳言独立、分割——但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又偏爱于独立、自足,讳言传播、交流。凡此种种,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受某种干扰——这与某家、某派在其研究中以某种思想原则为导引完全是两码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美术史研究中的框架、撰写史著的格局,或许可以明白,那种状况的出现和牢固树立,并非都是个人的自觉取向。
因此,撰写一部地区性美术通史,不仅可以有填补框架的意义,而且可以有矫正某些框架的意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地区美术史在某些阶段上往往无法吻合于一种预定的“时代精神”,而充分表现出独特而生动的个性,可以诱发出许多具体而有趣的问题——“我知道要回答这些问题决非易事,但我强烈地感到,正是这类细致入微的设问将取代Geistesgeschichte(精神史)的一般性概括。”(贡布里希:《探索文化史》)
二
在地区性专门史的研究上,其实早有前辈大师披荆在前,楷模未远。仅以一部新会陈援庵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已有无量烛照,惠嘉我辈后学。读《考》的收获,对于门外如我者,也可以有如是一二则:一是藉此而思考某区域在历史某阶段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如明末永历,“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陈寅恪为该书作的《序》);二是全书搜采赅备,闻见博洽,治于一隅之地,无论体制、识断,堪称精善无比;三是所述大势变迁、士人全节,种种慷慨,唏嘘后人,又岂可以佛教史论之而已。从这最后一点我们又可以联想到人文科学研究与价值准则的问题:“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如果人文科学想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它们就必须关心价值”,“我们应该归还人文科学的惊讶感、崇敬感、还有恐惧感。换句话说,应该归还人文科学的价值感。”(贡布里希:《艺术与人文科学的交汇》)读陈垣、陈寅恪、钱穆诸前辈大著,当可明白识见与价值信念的密切关系。钱先生在《国史大纲》开卷即申明“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令人动容。由“问学”而“谋道”,兹事体大,为学者当毕生以求。笔者自愧学殖浮浅、闻道尚远,然对此种境界,实恒怀“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的感慨。是书之作,容有百病,然闻道之想往,敢言尚存。
三
时人于广东美术,或即作某派某家之想,或至远而曰颜宗、林良,实为可惜。早在距今7000年,广东地区已出现陶器文化(青塘类型),而前此的粤西洞穴遗址文化大致与西亚新石器前陶文化阶段相当,有可能是我国所知现存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参看第一章第二节)。广东美术源头的幽远足以令人称羡,而广东几何形印纹陶的丰富性与艺术性远超出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安娜托利亚、爱琴海克里特岛、希腊、巴尔干、多瑙河地区的同类型陶器,也令人自豪。
从种类的丰富性而言,广东地区美术在某些阶段上显得稍为逊色,但在另一些阶段上却与中原等其他地区一样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本书各章中的节、目安排即根据该时期美术门类的具体情况而定,不强求一律。关于门类的划分问题,也是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的。作为一部地区性的美术通史,在资料来源等方面会更容易受到传统的“器”分类法的影响,因为许多考古、地方文物志、藏品介绍之类的文献是乐于沿用此种分类法的。而在美术研究领域中,学院派的传统是根据造型艺术的视觉审美性质而不是作品的材质来进行分类的,也就是划分为绘画、书法、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等几个门类。毫无疑问,笔者完全服膺和坚守这一分类标准。即使在出现边缘模糊的情况(如在工艺与雕塑之间常会发生的)下,也力图循其主要形象的基本特质而使之归入相对的属性之中。
无论从纵或横的方面来考察,“广东美术史”这个概念均有着丰富的内涵,而且会超过人们可能想象得到的。长期以来,作为考古、文物工作者的工作成果的这些丰富的资源基本上没有得到美术史家的开发和利用。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在某些人看来,这些资源中的绝大部分不会对说明他们的历史、声望等有所帮助,因而他们对历史研究的支持和倡导是会有所选择的。我继续猜想,这或许可以解释前面提到的一个小问题:一提起“广东美术”,许多人即作某派、某家之想。
笔者撰写本书的初衷,正是为了表明:广东美术有着远比某派、某家要丰富、广博得多——甚至是难以比拟的——历史内涵,美术史家可以有着非常辽阔的研究视域,而且可以离开某些事物很远、很远。
笔者相信,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书至少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四
在本书的写作研究中,笔者大量借重了考古学、民俗学、甚至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是与“美术品”直接相关的,而且涉及广阔的背景,正是在那里隐藏着许多美术史学的重要课题。比如,美国考古学家W·G·索尔海姆撰有《史前时期中国南部主人是谁?》一文,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广东原始美术的创造者问题。人类学家吴新智先生认为,不会排除马坝人与东南亚海岛古人类的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的可能性;美国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则深入研究了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在获晓其学术结论之前,笔者深感其研究预示着南中国人种具有极大的文化基因辐射力。这些研究强调了南中国历史的自我继承性和文化的辐射性,对广东美术的起源问题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创造出广东原始美术的作者应是土生的原始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融合为更具鲜明的文化特征的越民族。
又比如,陈列在广东省博物馆里的“人首柱形器”,关于它的性质与用途似乎一直是语焉不详的。而借重于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它是“猎首”(Headhunting)风俗的产物,并延续到南越国时期。这对于研究青铜器人像艺术(无论立体或线刻的),均有重要影响。
实际上在实证学科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诸如文化传播理论、解释理论、美学理论、艺术社会学理论等方面获益甚大。引入某种理论有时还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提出问题。
由于有了所有这些学术资源,我们可以运用或创立某些研究框架,使地区性美术史研究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均超出了地域的限制,而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
五
还原历史事实这仅是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的初阶,而在更高一层的台阶上,所要求于研究者的,是揭示出历史事实的价值、意义。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国学都归之于前者,但作为其主要倾向和侧重点,却是的确偏向于前者。西方人文学科则是对后者更为关注,贡布里希先生的著作则是在艺术学领域中给我们树立的、可以效法的典型之一。
中国人往往会把价值、意义等看作是虚的、很不实在的,但唯一的例外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接受并牢固树立了关于历史理性的体系——一个颇有黑格尔色彩的命题。在不少西方人看来,真实的价值会具有客观性和普遍可传达性。从康德到胡塞尔,他们都坚信这一点。
笔者在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久久迷惑于中国史学体系的国粹传统与历史理性力量的结合。后来这个问题是在史学之外找到一些解答的启示的。经过这种过程,我对从康德到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充满由衷的敬意,尽管对他们的思想学说所知极其有限。无论如何,一种深切的价值感和形式上正当的主观性是再也抹不掉了!
在上述这种思想背景下研究一种局部的、实证性很强的地区性文化史,我似乎在不自觉地运用着双重标准、甚至双重的叙事方式、口吻。这种芜杂不纯固然是“学”与“道”均远未成熟的表现,但同时标识着我的真实存在。我实际上是别无选择。
由于有了种种这些心路历程,《广东美术史》的写作之于我,竟然有了某种诗意的体味,就像一次让实存歌唱、令沉默的言说起来的对话。因此,我无论如何不会接受历史研究必是枯燥无味的说法——天知道在写作的这些日子里,曾经有过多少次密纳发的猫头鹰起飞在黄昏!
问题是,就像话一出口,词语的精魂便随风飘散、只剩下词语的躯壳达于彼岸一样,耗失的东西已经耗失了,只剩下一点痕迹夹在历史学式的文字当中,连我自己也难以钩寻。
本书论述的人物之一、新会陈白沙有谓:“除却东风花鸟句,更将何事答洪钧”,这种自得使一切苦役变成乐趣。我现在是体味得到了。
(出处:《广东美术史》,李公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广东美术史txt,chm,pdf,epub,mobi下载
广东美术史txt,chm,pdf,epub,mobi下载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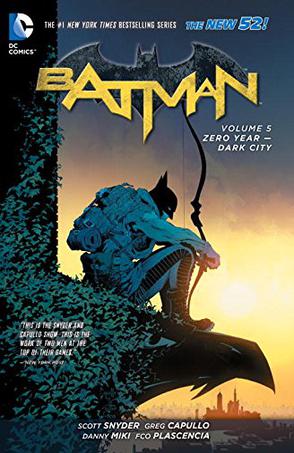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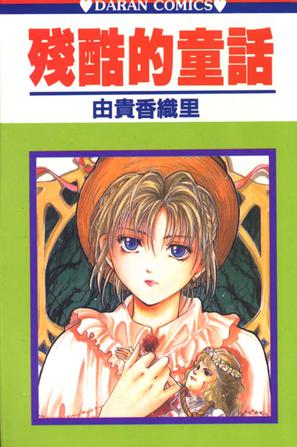
非常喜欢
买来学习
大大点赞!
都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