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的原始语境中发现历史
——魏中林等《古典诗歌学问化研究》序
吴承学
研究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古典学的学者,心态、气度往往不同。前者俯视平辈,直击现实,容易产生“一览众山小”的豪迈。而古典学学者面对悠久的学术史,仰望一座座高峰,更多的是“高山仰止”的敬畏。前人汗牛充栋的成果容易让古典学学者产生一种“影响的焦虑”。
如何有所创新,一直就是困扰和挑战古典学学者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曾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先生指出向上一路,陈义甚高。“新材料与新问题”确是极为重要的,两者结合自然是治学最上乘的境界。比如近代以来的敦煌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都是有赖于新材料而兴起的。像敦煌石窟与甲骨文等这类“新材料”的发现而引发的“新问题”,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如果古典学者一定要等“新材料与新问题”才进行研究,那就不免要守株待兔了。不过,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悲观踌躇。回顾一下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思想史,多数重要成果的取得并不是因为“新材料与新问题”的出现,而是由于新思想与新理念的引入。陈寅恪先生本人的成就也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新材料与新问题”,他的高妙之处,是在常人熟见处发现新问题,即是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中用新的眼光和见识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是更具魅力和挑战性的。
就古代文学而言,新的观念和见识固然可以借鉴外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但更应该从中国丰富的文学实践中提炼出来,将思想和研究的立足点回归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原始语境,回归到中国传统典籍内部所呈现的自然脉络,在中国本身的历史丰富性之中去不断发现和创造。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就提出:“所谓古代文学理论,应该包括‘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这两层含义。因而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就应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既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也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工作,其研究对象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二者虽然都是重要的,但比较而言,后者是更困难,也是更有意义的工作。”(《古典诗歌结构与描写中的一与多》)程先生的高论为我们提供了拓展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新领域的思路。如果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那就应该在现有的研究理论、概念之外,提出新的概念与范畴。
魏中林等先生所撰的《古典诗歌学问化研究》一书,它的最大的特点和亮点就是:它不是从外在的理论和现成的文学史框框出发,而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原始语境中,从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内部的脉络中,梳理了文学发展中一个长期存在却一直没有被充分关注的显见事实,然后把被隐没了的理论与被遮蔽了的事实再度揭示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古典诗歌学问化”。“古典诗歌学问化”正是立足于现有的研究理论、概念和文学史框架之边缘,所提出来的符合中国古代文学事实的新命题。我们借用程千帆先生的说法,这本书就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具体来说,也就是“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这正是它的独到之处,也是其价值所在。
我曾经说:“在古代文论的原始语境中,理论的‘生态’往往是平衡的,每种理论常常是和它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存在的。”(《“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中,以“性灵论”为中心的“意境化”与“学问化”实际上是相反相成地存在着。但是,长期以来,“意境化”问题占住了中国古典诗学的视野中心,而“学问化”的问题,虽然相关的如“学人之诗”等论题亦受到关注,但深度的系统研究整体上仍处于被忽视或被忽略状态。
作者所谓的“学问”并不仅是指书本知识,所谓“学问化”也并不就是掉书袋。“古典诗歌学问化”是指将诗歌创作与知识、学问、道理等修养联系起来看待,因此,本书的“学问化”的内涵是比较宽泛的。基于此,作者认为,“古典诗歌学问化”是自《诗》、《骚》以来中国诗学文化的一种传统。作者认为:“古典诗学学问化不仅是某一时期或流派所集中体现出来的片断性现象,而且是伴随着古典诗学历程强弱参差地形成一个持续性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趋向是以踵事增华的方式由弱渐强,越来越明显。”(《绪论》)本书从理论的高度上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对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古典诗歌学问化”进行史的勾勒与探讨。全书共七章,上至中国诗歌发轫的先秦时代,下至新文化运动,原原本本,追源溯流,系统地梳理了“古典诗歌学问化”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别出心裁的文学史。虽然,本书涉及问题面广而且历史悠久,观点或可商榷,文献容有未安,但是作为一部“问题发展史”,它必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我读完这本书,掩卷之余,不免思绪纷纭。
我们曾经以为文学产生于民间,产生于劳动,诗是一种纯粹感情的产物,而诗歌创作与知识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这些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但又不免片面。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民间就是天籁,到了文人手里,就往往折杀了诗的纯美。这就有些偏颇了。在文化史上,文人对于民间文艺雅化作用的积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消极意义。没有文人的记录、提升与传播,民间的性灵与智慧,可能很快就灰飞烟灭,无声无息。《诗经》中当然有些是采自民间的诗,但肯定是经过文人的选择、修饰、加工和提炼的。比如《诗经》首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些诗句很难想象纯粹是那些目不识丁的百姓信口创作的、纯天然、原生态的民间诗歌。其实,有些我们所读到的许多以为很“民间”的文学,也是经过文人与民间一批有知识的“秀才”记录与加工的。这个道理看看明代冯梦龙辑录的民歌就明白了。民间与知识绝不是矛盾的,更不是对立的。就像现在网络和手机上流行的那些极为机智的段子、民谣,当然可以算是民间的智慧了。但这些绝对不可能是那些文盲或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所能编造出来的,很可能是一批有“学问”的文艺青年在网上神思飞扬的集体结晶,也可能是一批文化和智商都很高的公务员在酒余饭后的湊趣逗乐。其实,民间社会也是可以“学问化”的。以今度古,想当然尔。
诗歌创作没有“性灵”不行,就像没有火种如何燃烧?光有“性灵”也不行,就像只有火种而没有充足燃料,如何能成燎原烈焰?性灵与学问都是诗歌创作不可或缺的要素。诗歌需要性灵,是不论自明的。诗歌需要学问的道理,则尚要饶舌几句。以李、杜为例。杜甫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自有神”,他的学问自然不必多说了。李白天才飘逸,似乎与“学问”无关。但李白也不是光会饮酒大言,他也是喜欢读书,也有“学问”的。他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的话也许略有夸张,但如果翻翻《李太白全集》,看看他所写的赋、表、书、序等,可以发现,李白还是挺有“学问”的。就是在李白诗中,用典与点化几乎在在皆是。就以被人读后惊呼为“谪仙人”的《蜀道难》一诗为例,就用了許多典故,腹笥极富。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著名诗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不读书、没“学问”的。如果没有浸淫于书林艺苑之中,传承悠久的历史文化,体味和领悟古往今来、人生社会的奥妙哲理,所谓的性灵,只能是浅薄而没有深度的。也许,灵光一闪,就转瞬即逝。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说:“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但紧接着又补充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学问化”的重点在于能“化”,学问是诗人的修养而不是诗歌的表现对象。“化”境就是自然而然地流露,而不是刻意展示。你可以感受到,却难以一一指出来。若能“化”,则知识、学问、义理都如水中着盐,无迹可寻了。若不“化”,那怕学际天人,学问反成了眼中之金屑。
我在读此书时,有个问题一直萦绕心中:既然“意境化”与“学问化”在理论与创作上都是并存的,为什么最终会出现“意境化”占住了中国古典诗学的视野中心,而“学问化”则被边缘化?对这种现象,我们除了判断其合理还是不合理,合乎还是不合乎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现象产生的深刻原因。我曾说过,在古代文论的原始语境中,理论的“生态”往往是平衡的,“但是,经过人们的阐释与接受之后,‘平衡’就被打破了”。那么,这种有选择性的阐释与接受的背后,肯定含蕴着中国古人传统的诗歌理想与美学观念。我们发现了理论盲点,然后把这些曾被遮蔽的历史展示出来,这工作很重要,但我们仍然可继续追问:这种“盲点”的形成,是否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集体的、有意的选择性“失明”?若是的话,那么,这种选择体现的是偏见和短视,还是智慧与深刻呢?这也许也是一个有趣的而且是深层次的问题。
我与魏中林教授相识已经二十多年。1990年,中林从苏州大学博士毕业,分配到暨南大学,而我则从复旦大学分配到中山大学。中林师承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专攻清代、近代文学。我与他专业相同,且年纪相仿。刚认识时,他还很年轻,但看起来成熟持重,气度不凡,性格豪爽而心思缜密,谈论则高屋建瓴而极富逻辑。当时,广东省古代文学的博士还相当少,我们一起组织了全省古代文学的博士联谊会,经常聚会,交流心得,讨论问题。后来,中林与我都任广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也多次组织古代文学的年会。中林每年博士、硕士毕业,也经常让我去主持答辩。那时,我们在学术交流上是相当频繁的。
近十年来,中林因为政务繁重,我们之间交流渐稀。但是,我不时还能读到他发表的学术论文。在行政之余保持学术研究,可以想象是相当艰苦的。不过,也许可以获得一种追求真实与自由的人生快乐。本书稿是中林主持的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是他与高足共同完成的。当中林把书稿传给我,命我作序时,我就欣欣然应允了。我能成为此书稿的第一读者,感受其智慧,领略其精彩,也是一大乐事。
我读了这本书稿,深有感触,又回忆起二十多年来与中林交往诸事,浮想联翩,漫录于此。虽卑之无甚高论,然仿佛与故人对床夜语,絮絮叨叨,拉杂而谈,不亦快哉!
2011年11月1日
书于康乐园郁文堂
魏中林,1956年生,蒙古族,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1 987年师从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攻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90年获博士学位,任教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先后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韶关学院院长等。现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清代诗学、近代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合作出版《清代诗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山水文化》、《词综注》、《宋代文艺理论集成》等著作九部,在《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广东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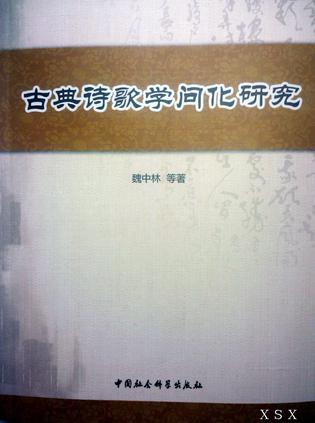 古典诗歌学问化研究txt,chm,pdf,epub,mobi下载
古典诗歌学问化研究txt,chm,pdf,epub,mobi下载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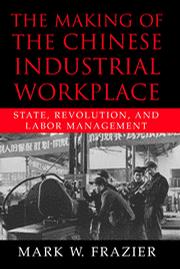


作者的思维的天马行空
经典
值得观看的一本好书!
很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