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比起卡夫卡的蟑螂要來得複雜得多……
盡是一些不可告人的祕密。
馮光遠、陳珊妮、張懸、蘇打綠青峰 合力推薦
這是一本最奇幻的都會寓言,最同志的異性戀小說。
大學新鮮人的第一要務,不就是要好好談個戀愛嗎?不過,愛好搖滾樂的阿怪,老是被身邊的女生當成「好姊妹」,害他跟女生談戀愛的可能性被一腳踩死;但尷尬的是,跟女生談不成戀愛,可是也並沒有半個gay真的跟他告白,或者試圖約他出去走走。
在天氣不穩的情人節晚上,他約了在Cafe 2.31認識的女生——阿妹,搶下客滿的加州風洋食館靠窗的位子(旁邊擠滿了開同學會與帶小孩的爸媽),先行翻閱了星座書(莎士比亞說:「談情說愛,還是隨大眾的意好些!」),在一道暴烈閃電過後,阿怪拿出一盒巧克力(屈臣氏買的,價格99元,一百元有找),對阿妹說:「情人節快樂!」阿妹生氣地瞪著他說:「你以為我是那種女孩,對不對!」
這個世界不是常人可以預料的,告白失敗的阿怪回家之後才發現全世界都變成了同性戀,在同性戀世界中,身旁所有的人對於異性戀阿怪投以大量的同情、狐疑、恐懼的眼光。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只有回到過去,才知道什麼造就了現在。一定有人在搞鬼,這世界才會突然一瞬間整個被轉過來。要解決這個謎團,只有回到「1982」!
■本書目錄
序 自由的幻象 陳珊妮
序 正常的世界 蘇打綠青峰
序曲
第一部 大衛與我
第二部 我愛鹹粥
第三部 大衛現身
後記
《1982》序:自由的幻象 文 / 陳珊妮
這本書可能變成你今年最重要的回憶,有多重要呢?大概跟女生們去除多餘體毛這種事情同等重要。然而若要再繼續追溯開始在意除毛這種事情的起點,我想約莫就是瑪丹娜唱〈宛如處女〉那一陣子吧!尤其看到她還在MTV台穿著粉紅色韻律舞衣扭得起勁……答應要替這本書寫點什麼字的承諾彷彿還是昨天的事,竟然一年就這麼過去了,年紀越增長對時間的感應越糊塗, 要不是有《火線交錯》這種電影肯定連催稿的記憶也會伴隨自責感完全消失,說真的硬是要我解釋這書,它比起卡夫卡的蟑螂要來得複雜的多,甚至跟黯然銷魂飯以及無敵風火輪引人發笑的原因一樣,盡是一些不可告人的祕密……
或許在今年的某個時刻打開這本書,或許暫時略過本篇不讀,或許你的人生就從這個點開始重新啟動。「一捲王子的紫雨錄音帶」——有人告訴我他的人生是從這裡開始改變的,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就好像我經常覺得友藏的俳句令人感動一樣。最近在朋友的新書裡重新看到了翻譯成中文的李歐納孔恩歌詞:「你打點好自己/你說/無所謂/我們都很醜/可是我們有音樂」——我曾經不斷想起這首歌,在那個只因為喜歡音樂,辛苦奔波綜藝節目通告的九○年代。
寫到這裡我還在片段式的反覆閱讀這本書,本來還以為只有伍迪艾倫才這麼碎嘴機車,但是在看《安妮霍爾》之前,我也以為沒看到第一幕就要翻臉的就我一個,沒錯!所謂的第一個鏡頭不外乎就是夢工廠東寶之類,然而我反覆閱讀這本書的原因正是因為這本書很反覆,引發某種瑣碎的自然趣味。我們大多數人的一生恐怕都要比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更瑣碎,也許稍微搖滾樂,但是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機率是令人沮喪的零。
雖然如此,我記得聽著性手槍的半成年蹺課天、奧茲奧斯朋的失戀男友、親吻了她的傑夫巴克里、拚了命熬夜工作的周杰倫,甚至輕輕鬆鬆就提醒著青春即將消逝的金剛腿鐵頭功……
我們或許是上天特別眷顧的一群人,我哼唱幾首歌,竟然有人已經寫了這部小說,改變部份未來,帶我們去了原本到不了的地方;U2的〈With or Without You〉正在電台播放,我們很少記得愛爾蘭,但是聽到熟悉的吉他前奏,偶爾憶起心碎愛人的臉,和眼前難得的幸福……
《1982》內文試閱 文 / 小樹
│1/2│1│2│
1.
我叫阿怪,可是我名字裡沒個怪字,連諧音的也沒有。記憶中大概是國三的時候就有人這麼叫我了,那個時候班上轉進來一個男生,聽說是從B段班來的,可是他不像上學期轉來的那個,數學比導師還厲害;這個傢伙功課普通,尤其國文簡直爛到無可救藥,我偷看過他的作文簿,那篇〈最美的夏天〉害我足足憋了一個星期,一見到他就想笑。可是我很喜歡見到他,我並沒有想捉弄或嘲笑他的念頭,我還想多看一點:除了作文簿,他的週記、車票夾,還有那種很香的畢業留言本,我全都拿來翻過了。
有一天,我又留下來幫老師整理考卷。天氣熱的夏天、心像寒冷冬夜。那首歌完全符合我當時的心情。功課普通但聽話的小孩就是會比功課好但不聽話或相反的同輩倒楣很多,前者叫不動、後者不敢叫,我就變成最好用的,乖乖地在同班同學都閃人後,憋著一肚子大便(這是真的),收齊分類一整天考得大家胡說八道(比方,[月經多久來一次、一次幾天]這種有幾個女同學佔先天優勢,在自己身體上就可以找到答案的題目,全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回答是四到五天來一次、一次二十八天。)的考卷,然後一個人回家。但是那傍晚離開導師辦公室後,我又繞回班上,習慣性探探那傢伙的抽屜,摸到一張他不小心掉在抽屜角落的大頭照,準備收進口袋的時候,居然被隔壁班那個住我家後面巷子的臭頭逮個正著:
「ㄏㄡ……我要跟你們班導說!」
「說什麼!」我賭他壓根沒看見。
「說你怪怪的,在人家的抽屜裡亂摸……」
其實我一回家就忘了這件事,只記得把臭汗酸的制服丟給媽媽洗之前要先把相片掏出來,夾在書桌的厚玻璃板下。我一直覺得他是因為長得好看才被調來的,否則留他在那夥抽煙嚼檳榔打群架的小混混裡頭簡直糟蹋。雖然他也挺結實,手球打得又好,可是他就是沒有那種耍狠露傢伙的兇氣;而且人都念到要考高中了,還會寫出類似「我覺得夏天很不好會流汗……」這種笨句子,他的個性肯定單純又可愛。
當天晚上朱小美跑來我家叫我跟她一起複習《歷史》一、二冊時,也看到了那張臉,她一直追問這個男生是誰?她也要認識。我心裡很不是味道,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吃誰的醋,朱小美說過要我跟她一起考進好高中好大學,然後手牽手一起出國,我還感動地小小親了她一下。可是她當時的表情看起來根本就已經無心教我什麼春秋戰國了,所以我就騙她說那是照相館老板放錯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誰。我想反正朱小美的學校在另外一區,應該沒那麼容易碰到。
可是,世界就是這麼小,隔天早上當朱小美經過他們學校糾察隊前面的時候,遠遠地就看到了他。 我真不敢相信她哪來的好眼力,竟然一眼就看得出走在一群都穿黑色運動服裡的那個頭不特別高大的他;他們正準備到縣立體育場去練球,朱小美完全不顧形象地大叫,還衝到人家面前說:「天啊,我們好有緣喔……」之類的。
當天午休時他就立刻把我拖到他們的球具間去問清楚,我還在想幸好臭頭沒有亂散播流言,否則一定更慘;眼前他大聲叫我一定要把照片還給他,我除了發抖還能說什麼。最倒楣的是,這一切又被罰勞動服務掃廁所的臭頭給聽到,結果放學前整個三樓二十來班的人都開始叫我阿怪。 「矮子矮、一肚子拐;說你怪、你還真奇怪! 」
我後來沒再見過朱小美,還有那個男的。我覺得自己被嚇壞了,心裡對男人女人都有陰影。
2.
升高二的時候,我又認識了一個女孩子。
這時候我雖然好不容易掙脫地心引力的侷限、突破了海拔一百七十公分,但仍是同輩中的低標。而頂上毛髮的生長態勢也日漸成形,它既不柔軟也不滑順,反而像一群黑林硬漢,傲然聳立,用盡什麼潤絲精跟護髮露都無法改變他們的立場,索性讓他們變成為我爭取身高排名的最後努力。所以當同儕開始把髮膠髮臘髮膏從仰望的高度拉到實際操作的層次時,我從沒想過打壓自己的禁衛軍,更加放任他們自由,朝天發展。
在同學眼裡,那不過是我黑框眼鏡後咕嚕咕嚕轉的腦袋裡,另一個大夥搞不懂的點子;但是對那個女孩子來說,卻代表著某種她會喜歡的品味。她說她對籃球校隊跟學生代表都沒興趣,因為才華與獨特性是唯一的標準。
她也知道我的綽號阿怪,我開始覺得那是一種恭維,因為讓我覺得自己真的有點不一樣。雖然她的名字早在我的記憶中遺失 但當時她就是懂我那些撐著場面亂聽其實自己根本也不懂的姿態。她也聽「史密斯」(The Smith)與「非法利益」(The Velvet Underground),我們還一起合買了原版《絲絨金礦》(Velvet Goldmine) 的DVD,在她家看得似懂非懂,但是我們都因為那部電影而愛上那個「華麗有理‧扮裝無罪」的年代,覺得大衛‧鮑依(David Bowie)真屌。可是一直要到我們有次混進校外的畢業舞會、她堅持要給我帶上一頂插滿紫色羽毛的牛仔帽的那一刻,我才好像懂了她真正的想法。
「不要啦!妳幹嘛啊?……」我抵死不從。
「你不是Gay嗎?」
「我為什麼是Gay?」
「不然幹嘛大家都叫你阿怪,你又從來都不碰我。」
「我…我…妳又沒說可以碰妳……而且,我們這樣聽搖滾樂就很棒了啊,不一定要這樣吧……」
「我還以為我了遇到很特別的人說……」然後她就哭了。
那一刻,我滿腦子迴響著《絲絨金礦》裡Placebo重唱的華麗搖滾經典"20Th Century Boy"
“20Th Century boy / I wanna be your toy / 20th Century toy /I wanna be your boy”
後來日本漫畫家浦澤直樹拿這首歌開啟了新的連載,但那時的我在那一刻真的以為這世界大概不會有女生喜歡我了。
3.
人的生命中顯然藏有很多轉彎,可是你從不會知道那紅燈不小心右轉之後,會不會躲個警察在行道樹裡?
又遇到臭頭,是大一新生訓練的下午。我幾乎認不出是他,他現在高出我半個頭,練得很精壯,而且一副話不多的害羞大男孩樣。說實在的,我承認他現在頗像個樣,眼光忍不住跟著那一身淺棕色混紡格子衫、搭著刷白牛仔褲的風景轉了幾圈,但我還是希望他沒看見我。
不過入學後發現我們居然是同一班時,我就有種要倒楣四年的壞預感。兩個星期後上第一堂「創作概論」,他乖乖地坐在角落靠窗的位子,不知情的人會當真以為他就是個內向安靜的人,我一方面不想理他,卻又暗自期待他那種初來乍到、假裝出來的鬼德性趕快破功!整堂課我都顯得坐立難安。
講師放了《血灑暴力牆》(The Wall),要我們討論其視覺構成與意涵。我發現班上完全沒有人知道「平克‧佛洛伊德」(Pink Floyd)是幹什麼的,也沒人注意到導演亞倫‧派克(Alan Parker)就是後來拍出瑪丹娜《阿根廷,別為我哭泣》(Evita)的那隻。我雖然懂得也不多,可是一路都是我在回答問題,連柏林圍牆拆除紀念演唱會都扯出來,還鼓勵大家應該去聽聽這迷幻搖滾的先驅:「……起碼要有一張「月之暗面」(Dark Side of the Moon) ── 就像你可以不喜歡U2,CD架上也要供奉著一張『約書亞樹』(The Joshua Tree)是一樣的道理……
「這位同學,」講師忍不住拿起他手中的點名簿,「請問你叫……?」全班一片靜默,我開始後悔自己幹嘛這麼多話,無形中成了人家的標靶。在一群昏睡的表情中,我隱約覺得臭頭在伺機而動。
「阿怪。」完了!果然被他先下手:「他叫阿怪啦!」
這一攪和,那些原本半瞇的眼睛都睜開來了。
「阿怪?真是人如其名。」全班第一次整齊地笑開。
「媽的!你這死臭頭!」我急著反咬回去,恨不得真咬他兩口!
「誰是臭頭?」
「你還想賴啊!你就是我國中隔壁班那個專門愛亂傳別人八卦的大臭頭,不然你怎麼知道我的綽號?」
「你認錯人啦!」
「什麼?」
「我不是臭頭,我是他弟,每個人都說我們長得一模一樣,簡直是雙胞胎。可是你真的認錯人囉!」
現在可好了,這場對手戲我馬上就要輸了,更糟的是,所有的人都看得很專注。
「哼!」我希望這聽起來像是一聲冷笑。怎麼會有這種事?我們的生活是一套少女漫畫嗎? 「你少來,想唬我啊!」我一回嘴,又爆出一陣哄堂大笑。
「好啦!好啦!不要說我們不開明,」我前面一個滑頭小子立刻跳出來,「你們兩個老情人好不容易有緣重逢,我們是不介意兩個男人談戀愛啦,但是要鬥嘴可不可以私下開房間解決…哈……」這下他們簡直是在歡呼了!
我恨臭頭!還有什麼臭頭的鬼雙胞胎弟弟!我知道他在唬爛,我生平第一次冒出報復的念頭。
於音樂圈入行十年,待過電台做過電視編過雜誌寫過報紙碰過網路混過夜店,很怕遇到自稱什麼音樂都聽的傢伙,曾任衛視音樂台的音樂編排主任、中國時報年度十大西洋專輯評審、第十六屆與第十七屆金曲獎評審、Hitoradio.com開站紀念盤《FC5-118》音樂統籌、台北縣第二屆音樂影展評審;現任Hinoter映象集總編輯、Hitoradio.com編輯主任、Hit FM Chill-Out Zone DJ、4 plus 4周五與Barcode周六駐場DJ、La Vie雜誌專欄作家、KK Box特約樂評,瘋狂愛樂程度至今未減。
 1982: 21st Century Homophobic Boytxt,chm,pdf,epub,mobi下载
1982: 21st Century Homophobic Boytxt,chm,pdf,epub,mobi下载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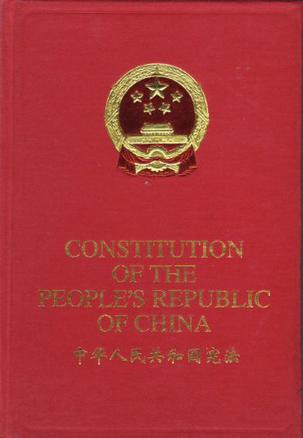
看以后要不要多看几遍,慢慢嚼。
很精彩,观点角度十分有趣
回转曲折,坎坷不平
原以为会很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