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人们通常把司法机关描述为一个与其他政府分支“相互平等”的分支,但就大部分美国历史而言,这种“平等”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恰切地把司法机关称为“最不危险的部门”,因为它既没有武力强制执行其判决,也没有钱换取服从。但是,1969年,当担任首席大法官16年之久的厄尔•沃伦退体时,“沃伦法院”这个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同时,也没有人再怀疑最高法院是一个与其他政府分支相互平等的分支。
在其简短的《沃伦法院与正义追求》1998年版首页上,哈佛大学教授莫顿.J•豪维茨写道:联邦最高法院“常规发布的判决改变了美国的宪法原则,并随之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这将“日益被视为美国宪法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革命性篇章”。大卫•奥布莱恩广受传颂的《风暴中心》开篇有个大标题,恰如其分地传达了最高法院现在的实际情况:“不再是‘最不危险的部门’。”
《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有两个目标:其一是促进在美国政治背景下讨论最高法院这一宝贵传统的复兴;其二是综合大量有关沃伦任职期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及其裁决的书文信息,以取代以往的陈词滥调。虽然这两个目标基本上可以自圆其说,但每个目标的合理性也许需要在一开篇就有个简略的交待。
在像普林斯顿大学麦考密克法理学教席拥有者这样的重要人物领导下,联邦最高法院与政治相得益彰的最高法院学术流派一度蓬勃发展。执这一教席的人依次为:爱德华•s•考文、艾尔菲厄斯•托马斯•梅森和怀特•F•墨菲,哈佛大学的罗伯特•G•麦克洛斯基也位列其中。当时,政治科学家和法学家一样都对联邦最高法院产生了兴趣,各重要政治科学期刊也定期发表该流派的文章。但是,这一流派却在25年前消失了,我们也随之失去了对联邦最高法院的重要洞察。
律师和法学教授在本性上和专业训练上皆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中心,他们倾向于认为法律相对于大社会或多或少是自治的。政治科学家则更多地对此表示怀疑,他们通常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受制于大社会内部的各种趋势和压力。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变化席卷了整个学科。首先到来的是定量研究及其精确度的诱惑,但对那些不大迷恋统计学的人而言,接踵而至的是理论的变化。各政治科学院系似乎不时出现惊人的分裂:一些教员嘎吱嘎吱地咀嚼数字;另一些教员嘎吱嘎吱地咀嚼理论,没有一个关注政治本身。尽管这只是一个讽喻,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至少还有公法这一领域,其中心就在于把最高法院作为行使司法审查权的宪法法院—— 它离今天如此之近,以致显得不那么真实。
政治科学的转向将已经有点边缘化的公法进一步边缘化,并导致选择依据定量资料,或更可能是依据理论来分析法院的公法学者不断减少。在下述事实中.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政治学脱离最高法院分析的转向和公法的衰落:在麦克洛斯基于1969年去世后,尽管哈佛大学用他最杰出的弟子马丁•夏皮罗来代替他,但是,当夏皮罗于1974年重返加利福尼亚时,他并未做进一步的努力来保持现存的传统。同样,在墨菲退休后,普林斯顿大学也听任麦考密克教席空缺。今天,发表在政治科学期刊上的一篇关于最高法院和政治的非定量文章,就像法学期刊上的物理学文章一样显得突兀不堪。
1969年,政治科学家乔尔•格罗斯曼和约瑟•坦嫩华斯把他们编辑的那卷《司法研究前沿》的主打论文命名为“迈向公法复兴”。很不幸,他们的乐观不合时宜。事实上,公法正在滑向深渊:考文和麦克洛斯基去世了,梅森退休了,墨菲众多的学术天分也正将其引向别处。
近来,夏皮罗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政治科学:学科状况II》(资深教授回顾各自领域的文集,Ada Finifster,ed.,1993)修订本中,多次提到公法“非常成问题的状况”。夏皮罗总结和分析了公法不幸的状况:“令人震惊的是,包
括哈佛、耶鲁、芝加哥、密西根和斯坦福在内的许多顶尖政治学系里都没有主要从事公法教学的资深人士。”就在不久前,墨菲的退休使普林斯顿也名列其中。尽管如此,由于美国政治学者停止与其公法同行讨论,这使人真实地感觉到公法的内部毁灭已无关紧要。“公法因此缩成了一个边缘化了的宪法——最高法院隔离区,其他政治科学家几乎不感兴趣。”为他的想法完整起见,夏皮罗也许还应该加上:“并且法学教授对它也没有兴趣”(法学教授早就不再看他们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同行写的东西了)。
正如夏皮罗所言,尽管政治科学内部的转变很大,但沃伦法院本身是造成这一困境的同样重要的原因之一,用夏皮罗的话来说,这个困境即“好几代博士被消耗了”。沃伦法院激励了年轻一代律师,吸引了更多学生学习法律。同时,当“不再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成为一代人的口号时,70多岁的厄尔•沃伦和威廉姆斯.O•道格拉斯却成了大学校园的偶像。对公法感兴趣、本来可能进政治科学院系的学生大都转投法学院。原因很简单,沃伦法院是最刺激的地方,宪法在法学院也处于一枝独秀、无可挑战的金字塔尖(联邦最高法院对使宪法史边缘化的现在和将来的潜在承诺)。结果,政治科学院系公法的招生受到严重限制,公法学术水平也持续下降。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流逝,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法学教授的手里。就法学院的训练和社会化程度而言,这意味着政治事件在解释判决行为和结果时被赋予了一个微乎其微的角色。
本书试图复兴这一最高法院学术流派,该流派关注最高法院裁决与全国政治之间的关系。通过寻求对联邦最高法院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进行解释,我完成了一个学术性(并定期从业的)宪法律师的任务,这(极大地)受益于我为威廉姆斯•O•道格拉斯作助手的经历(在本书书末所述事件后的那一年)。作为一名律师,我审视了案件的独特事实,审视了律师现成的和已经提出的论据.审视了大法官用以回应的法律手段,这些手段受以前判决以及九人团之内制度和个人安排的影响。我用政治科学和历史的眼光补充律师的看法。制度安排至关重要,判决不会在真空里产生。法律不仅仅是政治,但法官们清楚其判决的政治背景,与其他每个人一样,他们也受到了美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潮流的影响。
辅以法律和律师的眼光,司法决策的政治科学会更好;辅以政治科学的眼光,宪法律师职业也会更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理解这种协作。因此,在重要性上,我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新颖、也不惊人,但是,我们还理解这种协作吗?这一点不再清晰。因此,在另一种意义上来看,既然我所采用的方式在超过1/4个世纪以来都很罕见,就肯定会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法学院和政治科学系都有一些年轻学者致力于法学和政治科学的结合,我乐于加入他们的行列。曾经有过宪法律师和他们政治科学领域的学术同行阅读、理解并受益于彼此作品的时光,我期待它的重现。
事实上,关于沃伦法院的很多信息,尽管公众不知晓,但最高法院的学者已经知悉。然而。没有人试图把这些信息综合成一部全面的历史,我这样做是希望即便是专家。也要以新的视角看待联邦最高法院,处处留心新的动态。
为什么还没有一部综合的沃伦法院历史?这有很多原因,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似乎一提到沃伦法院,每个人就都变成了党派分子。结果,沃伦法院的支持者和诽谤者同时非常有代表性地把它定型化了,以至于它实际上是什么和做过什么都成为快速概念化的牺牲品。关于沃伦法院的文献资料的最主要特征是一味地欢呼雀跃、歌功颂德,作者们通常对联邦最高法院大加赞扬,尽管有些人开始以蔑视的态度埋葬它。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沃伦法院都是今天的一个窗口、一块确定正误的试金石,这种方式对律师和政治科学家是有用的。人们必须意识到,与塔夫脱法院或者富勒法院一样,沃伦法院已经成为历史。过去在沃伦成为首席大法官时就在教书、现在仍在教书的那些人,早就有资格退休了;所有不超过50岁的教师,都是在沃伦退休后进入研究生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沃伦法院也应该像其前任们一样,值得从更远的距离进行历史观察,而非工具性地服从于当代的政治目的。
我坦承自己曾是个盲目拥护者,我赞美自由主义的胜利,并对其退缩感到沮丧。但是,多年的学术生涯给了我不同的看法。我的工作既非欢呼也非嘲笑,而是理解与解释。1964年的选区重划案(Reapportionment Cases)或者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Arizona)判得对不对,对我而言不再紧要;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Education)则不同,它的正确判决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对所有案件而言,都应该理解联邦最高法院为什么这样决定以及它试图如何决定。我们是否赞成判决与它们的重要性无关,也与作用于联邦最高法院产生这些判决的力量无关。
沃伦法院行为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存在巨大的解释性争议,但也有重要的一致性观点。学者们似乎同意,沃伦法院由一群强有力的、有天赋的人组成,他们比其前辈们更加追求平等主义,也更同情个人权利主张;他们更愿意介入有争议的论战,更倾向于不受以往传统的羁绊,更相信国家解决方案优于地方解决方案。我关心的不是这些变化的好坏,而是它们从何而来、走了多远以及它们最终如何遭遇限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希望避开法学教授们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中心的研究传统,把联邦最高法院作为三个相互平等的政府分支之一,因为这三个分支都对美国政治及其文化思想潮流产生影响,并受之影响。
本书的写作离不开桑迪•莱文森的友谊与鼓励,他是麦克洛斯基的另一位杰出弟子,20年的光阴证明,他实乃理想之同事。得克萨斯大学政府系延长了对我的一项联合聘任,否则我也不可能写作本书。系主任吉姆•菲斯肯最先促使我教授一门关于最高法院的课程,其后他又不断鼓动我把自己的想法撰写成书。
在写作如此庞大的一本书和讨论范围如此广泛的判例(大多数是宪法性判例,尽管联邦最高法院的非宪法性裁决在数目上远远超出更为重要的宪法性裁决)的过程中,我得益于很多朋友无偿的帮助和建议。桑迪•莱文森、迪克•马克维茨和H•w•佩里不止一次地阅读了本书的每一页。汤姆•克拉特马克阅读了本书大部分章节。本书写到一半时,我遇到了怀特•墨菲,他给了我很多评论;更为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一个接触其知识宝库的机会。沃尔特•迪安•伯纳姆、乔治’迪克斯、辛迪•埃斯特伦德、马克•格根、杰克•格特曼、马克•格雷伯、萨姆•伊萨克罗夫、道格•莱科克、大卫•拉班、乔丹•斯泰克和查尔新.艾伦.怀特在其各自的专业领域对本书的各个部分做出了评论。我很想说所有可能遗留的错误都是他们的,但恐怕还是我的。
塔尔顿法律图书馆的一贯兢兢业业的优秀职员罗伊•莫斯凯为我的写作作出7惊人的贡献。我特别感谢政府文件管理员芭芭拉•布里奇斯、参考部的马林•鲁滨逊和负责汤姆•克拉克文件的档案管理员迈克.维德纳。我同样受惠于大卫.冈恩,他后来离开了塔尔顿,前往私人部门就职。我找不到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我对塔尔顿法律图书馆职员的谢意,他们真是树立了优秀的典范。
我的长期秘书康斯薇洛-埃金记录了对我很有意义的草稿,并把它整理成了出版者希望看到的样子。她也发现和纠正了很多我在多次检查中都没有发现的错误。
除了我的朋友们之外,我必须提到两位年轻学者,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宪法历史学家迈克尔-克拉曼和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杰拉尔德’罗森堡,他们写出了关于联邦最高法院与社会变革的重要作品。他们的著述时而与我的重合,并一直帮助我澄清和阐明自己的想法,即使是在我与他们中的一位或者另一位(或者两位都) 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们的影响遍布全书,即便在随后的注释中未予注明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麦克洛斯基和墨菲的作品给我的启示,我还可以回想起30年前我读他们的书时那种“这就是学问”的感觉。
最后,用一句话说说尾注。经过挑选,本书的注释很少,一般用于直接引用,几乎很少用于其他情形。最后的参考书目是对那些提供了很大指导的资料来源的答谢。引用最高法院判决之处没有注释,判例索引提供了相应的引证。
 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txt,chm,pdf,epub,mobi下载
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txt,chm,pdf,epub,mobi下载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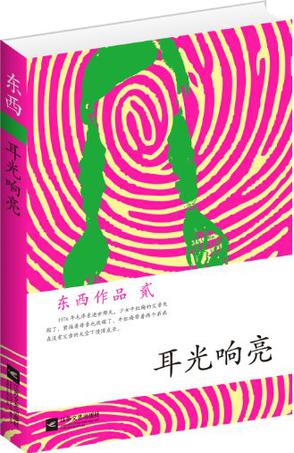
非常满意
经典
一季一寂思年华,繁华落尽惹尘埃!
“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有身份的问题,人类永远不可能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