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貼著桌緣上方,縫著珍珠色鈕釦的襯衫從中央到右邊,有一道暈開的血跡,心臟部位插著一把細長的裁紙刀,血就從露在外頭的刀柄處滲了出來。血,我模糊的想著,看起來真像乾掉的紅墨水……
沒留下姓名的第一個冷硬私探
古希臘的柏拉圖相信萬事萬物皆存在一個「原型」。圓,是絕對的圓;桌子,是絕對的桌子;正義,是絕對的正義。相對來說,我們的人生現實中有無數的圓形,有數不清的桌子,和紛云不定的正義說法和主張,但這些都只是現實不完美的摹本,原型永遠只有一個,完美,絕對,只存於理念之中。
對早生了兩千多年的柏拉圖,我們顯然來不及請教他:如此,您老人家認為冷硬派私家偵探的原型該是什麼樣才是?
在柏拉圖並不熱中的現實界中,我們倒不難找到這個原型,那就是本書奉他為名的「大陸偵探社探員」,老實說,離開柏拉圖的完美不可以光年計。他中年(三十五歲)、矮、而且肥胖。不漂亮當然沒關係(記住,我們在看的是偵探小說,可不是羅曼史),不漂亮當然也仍可以很迷人,像克麗絲蒂筆下也是矮胖造型的白羅探長,他有顆奇特的蛋形腦袋和永遠用蠟漿來尖翹的大鬍子,充滿智性的幽默和老式歐陸貴族的美好鑑賞力;或像福崔爾筆下的「思考機器」范杜森教授。絕大多數人可能記不清他外表長相如何,但我們一定難忘他那顆碩大無朋的奇異大腦袋,也一定記得輸給他的蘇聯籍西洋棋王所說的話,「你不是人,你只是一個腦子——一具機器——一具思考機器。」
這仍是極迷人的某種偏執天才科學家的美好造型,像愛因斯坦那樣。
然而,無名大陸偵探社探員這些一樣也沒有,甚至他的姓名我們都不知道,沒人崇拜他,也不會有女性傾慕他,偶爾若有哪個女生願意陪他上床,無非是案子犯到他手裡,想藉此手段脫身罷了(但就我個人所知,沒成功過)。
在後來的長篇《紅色收穫》中,這位無名探員有這麼一段自白:「瞧,今晚我坐在威爾森(該案委託人)的桌旁,玩弄他們像玩弄鱒魚似的,玩得很開心。我看著努南(該案中的流氓警察頭子),知道因為我對付他的手段,他沒千分之一機會再多活一天,我笑了,覺得內心暖洋洋的很快樂,這不是我,我一身硬皮,只剩下靈魂了。經過二十年和罪犯鬥法,我可以面對任何謀殺案,什麼都不看,只看到我的飯碗,看到例行的工作……」皷
兩個並不矛盾的出處
漢密特曾說,「當代(他說話的那時候)小說家該做的工作就是,從真實生活中切割出一部分來,讓它們直接呈現在白紙之上,而且,若更直接從大街之上移到紙張之上,小說也就理所當然更真實。」
大陸偵探社探員這個原型顯然便是尊此要領來的,它更具體的來源,漢密特一度宣稱,係立基於他平克頓偵探社巴爾的摩分社的一名同事叫詹姆斯.賴特(James 眍Wright)的;然而他也還講過,其實這個中年悍將的人物造型基本上是綜合性的,由眾多他認識的人你一小塊我一小塊組合而成,出處不止一個。
這兩種全出自原寫作者之口的說法到底哪個對?我個人的想法相當鄉愿,我以為兩者應該都接近事實而且彼此並不矛盾——對小說創作活動有基本理解的人都曉得,小說中人,尤其是主體人物很少是完全憑空「捏造」出來的,他往往借助了某一個真實人物的名字、身分、職業、外表特徵、某段有趣的遭遇或更內在的某一個有趣的心理狀態為起點,再以這個點為磁場中心,吸入小說家所要的其他材料組合而成。
說真的,這個點是哪個人或在何處,往往之於讀者半點也不重要,就像我們這位大陸探員的造型起點究竟叫賴特或叫傑克根本無所謂。絲毫影響不了閱讀;但對於創作者而言卻往往生死攸關,因為他所面對的創作想像世界是廣袤的、自由的、無界限的,創作者需要找到一個點(儘管可以是任意的、隨機的),做為標示座標的原點,讓他的想像啟動而不至於漂流;或說做為想像的起跳點,如此他才能安心的開始縱跳,如〈易經.乾卦〉的第三爻所說的,「或躍在淵,吉,無咎。」——意思是,想試著飛上天的龍從水面開始縱跳,就算不盡成功,落下來的地方仍是水淵,不會有危險。
一種純粹的自由是令人迷惘的,就像古希臘的數學家完全不曉得該如何料理「無限」這個概念一樣,生命,是從有了界限開始。
白被單的寓言
想像力華麗、豐沛,到令人不可逼視的哥倫比亞籍小說家賈西亞.馬奎茲,在他的鉅著《百年的孤寂》書中,乾乾淨淨的只憑著一張白被單就讓美人兒昇空而去,這讓全世界努力想讓他筆下人物也飛上天去的小說同行瞠目結舌(原來就這麼簡單啊!),然而,我們說,即使是馬奎茲,仍得靠著這一張有著明確物質屬性的被單才漂亮完成這件事。
馬奎茲曾如此說過,「沒有寫實基礎的憑空想像是最難看的。」
沒錯,這裡我是忍不住把馬奎茲的美人兒大白天昇空、尤其是昇空所用的白被單當成某種創作的寓言。我以為,一般讀者,甚至更嚴重包括不少的小說寫作者,往往對想像的無羈無限存著過多的「想像」,以為只有那裡才是創作者該去的允諾之地;相對的,諸多不完美的、沉重的、多限制的、乃至於醜惡的現實世界,是想像的大敵,應該用力對抗奮力掙脫——這樣的意念被過度上綱,使容易生出馬奎茲所謂的憑空想像,俗名叫「亂想」;從而寫出馬奎茲所謂的最難看的作品,俗名叫「亂寫」。
李維史陀和逼真畫
人生從現實世界開始,文字符號取樣於現實。繪畫臨摹現實,傳說和書寫濫觴於現實,人類和這個現實世界相處了數千數萬數十萬數百萬年,長期在這樣地心引力的拉扯之下,的確有不堪其擾之煩,就像柏拉圖《理想國》中所描述的「洞窟理論」一樣,人生所謂的現實世界中的處境,正如被鐵鍊禁錮於山洞中的囚徒一樣,它阻止了我們更上層樓看到另一個更鮮明更完美的理念世界——所以古希臘的哲學家寧可仰望星空、遊徜於數學的理知之中,印度佛家揭示了眾多更美好、清涼有香氣的不在現實裡的世界,文學的浪漫主義要用意志和想像來替代模仿現實世界的苦工,繪畫的印象派極力想掙脫我們肉眼所見的一成不變實物實相云云。瞻望並尋求超越,也一直和人類同在。
然而,李維史陀在他《看.聽.讀》(Regarder眍Ecouter眍Lire)書中評述十七世紀法國畫家普森(N. 眍Poussin)時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在繪畫的世界中,逼真畫的力量始終不衰?儘管印象派棄絕它,有識之士嘲諷它(如盧騷說:「俗套之美除了克服艱難之外似乎別無長處。」巴斯卡說:「繪畫具有何等的虛榮,它以事物的相似來引起人們的讚歎,但在此同時人們卻對原物毫無欣賞之意。」),更銳利捕捉實物纖毫的攝影器材出現一度更讓人們相信逼真畫已被替代、該落入到歷史的灰燼之中了。然而,那種以假可亂真、葡萄覆著一層果霜、花瓶的瓷器質感、乃至於馬兒彷彿要躍出紙外的繪畫仍吸引著人們的目光。
李維史陀的回答是,「這並不偶然,它發現並表明,正如詩人所言,無生命的事物也有著靈魂。一塊料子、一件珠寶、一只果子、一朵花、一件餐具,跟人的面容一樣,皆擁有內含的真實性。」「(畫家)通過某些技術程序,奇蹟般獲得敏感世界瞬間即逝的和不可捉摸面
貌的融和。」
李維史陀進一步指出,逼真畫並非單純的實物複製,而是再造,畫家必須專注發展對客體(繪畫對象)的深刻認知,並同時進行深刻的內省,以求得客體和主體的完整融和。便是在這樣的過程中,逼真畫截然分別於實物單純複製的攝影,也有別於直接繪製彩色照片的所謂新形象藝術派(李維史陀刻薄的用「倒盡胃口」來形容這支繪畫流派)——李維史陀並銳利的補充道,真要追究起來,稱得上優美的照片皆出現在照相機才發明的早期,只因為彼時的器材簡陋,逼令藝術家不得不投入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時間和自己的毅力。「人的手比起人的腦,仍是個很粗劣的器械。」
很清楚,李維史陀認為,原子排列緊密的物質並非就沒有感受、思維和想像迴身的空間,不必像柏拉圖(以及印象派畫家等等),非要斷裂開來到真實事物之外去尋求不可。
強大的抓地力
讓我們回到漢密特和他的大陸探員來。
由此,我們發現,漢密特成功創造了這個冷硬私探的原型,但他自己的解釋有著缺陷(小說家的自我解釋不如作品本身,這是常見的事),因為大陸探員並非直接「切割」自他那名叫賴特的同事,事實上,大陸探員擁有更多難以記敘(意識裡或潛意識裡)的經驗來源,並大量摻加了漢密特本人對這個世界的種種感受、主張、想像和價值,這正是李維史陀所說的主體和客體的完整融合。
或者,我們應該這麼說比較對:漢密特襲自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寫實主張,無疑是一種太簡略、太拘泥於「單一事實」的看法,這個看法並不準確且已然過時,然而,這並不足以讓我們急急遑遑得到非此即彼的完全另一端看法,認為寫實只是現實事物在白紙黑字上的移植,有想像力的人不屑為之。
千萬別低估了「真實」在小說創作世界中的價值。
較之李維史陀所稱,逼真畫在繪畫世界中始終不衰的力量,真實的人事時物之於小說的力量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它擁有強大的抓地力,給予小說和這個世界難以言喻的複雜聯繫,這種飽滿有力的聯繫往往不是創作者的意識所能遍及並設計得出來的,它也為小說鑄造了堅實的底子,令想像變得簡單而專注,不必屢屢回首來尋求最終的合理性——真實,某種程度是規約了想像力,但終極來說,它釋放了想像力。
更重要的,它沒讓想像把小說帶到純遊戲的世界,而保留在人文的思省之中——即使,看起來這只是一部消遣有趣的類型小說而已。
 大陸偵探社txt,chm,pdf,epub,mobi下载
大陸偵探社txt,chm,pdf,epub,mobi下载 首页
首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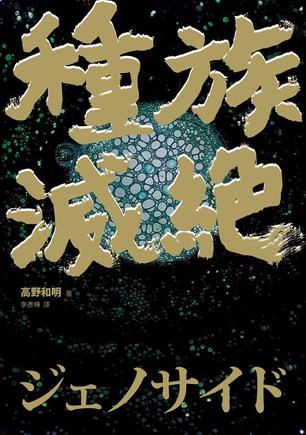



希望不会让我失望。
必看书目之一,很多年前就有所耳闻,现在终于入手了
需要细嚼慢咽
本书需要耐心的仔细品看,因为有些内容还是满学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