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方世界的十面埋伏--序《十個男人有詭異》 葉輝
我一直都以為自己——像董啟章在Sebald,Gould, Said-Ghost on the Shelf這篇小說裡所描述的調查員那樣,對詭異小說或電影心存抗拒,因而讀得極少。可是讀了本書十名男子的十個詭異故事——猶如那個調查員閱讀了當事人的日記和著作,才發覺自己其實不但毫不抗拒,而且邊讀邊勾起相近的閱讀記憶,只是從沒想過像本書的策劃人那樣,把類近的文本歸納於一個稱為「詭異」的框架。
董啟章的Sebald,Gould, Said-Ghost on the Shelf拼貼了三名已故外國作者的三段引文,調查推理與文本解讀(也就是與「書架上的靈魂」對話)並行不悖,甚或互為因果,喻意互涉,讓我想起阿瑟.艾沙.伯格(Arthur Asa Berger)的《驗一個後現代主義者的屍》(Postmortem for a Postmodernist ):被譽為「後現代主義之父」、擁有文化權力的大學教授,主持一次會議,突然短暫停電,燈亮後,他已被謀殺,身邊聚集著一群經典的、具謀殺嫌疑的人物:可能有情夫的漂亮妻子,年輕聰明的法國學者,肥胖的俄國語言學家,年輕貌美的女研究生,雙性戀的英國作家,疑是同性戀者的日本女教授……那是一個拼貼式文本,借推理小說的殼,混雜了胡鬧、戲謔、仿後現代主義插圖普及本……可以想像,探員為這批學院中人錄取口供時,必然對會議內容──大量夢囈似的後現代論述及圖像──感到茫然。有趣的是,上述兩個借殼文本的結局,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伯格戲謔到底,最終讓探員宣布︰「……即使你們沒有一人相信元敘事,而且都有殺死教授的上佳理由……我假定你們都是無辜的,不打算檢控任何人。我以為,公平地說,他的死是極之微妙的後現代模式。」讀者以為故事就此完結,揭過兩頁後現代圖像,才是最後一章︰雙性戀的英國作家著手把此宗命案寫成小說──教授死了,奇怪的是,他臉上凝結了似是會心微笑的神情;董啟章在最後一頁筆鋒一轉,調查員約晤了當事人(一位作家,他說家人去了「玩水」),以為結案了,翌晨閱報,才知道作家一家三口乘車墮進水塘──案發於他與作家見面之前。
也許,更有趣的是,伯格寫小說,只是玩票性質,他大半生在大學教書,是個口味博雜的流行文化學者,甚或可稱他為雜家,他曾提出解讀一個酒吧笑話的八種方法,對幽默和幽默感也有發人深省的見解,三十多年來寫作不輟,研讀大眾/分眾媒體話語、漫畫、笑話、電影、廣告、肥皂劇……的著作凡三十多種──本書的十位作者何嘗不是雜家?何嘗不是多面寫者?他們有些躋身於學院,有些逍遙於民間,可都像伯格那樣對世界充滿好奇心,對不同類型的文化書寫有極好的胃口,這一回,他們一人寫一個詭異故事,合成一冊,顯而易見不僅僅是一本怪談式的小說合集,在我看來,更可能是本港第一本借小說的殼而混滲了不同文化話語的bookazine。
如此說來,朗天的〈有的話總是有的──我的恐懼日記(給馬色爾)〉自編自導自演略帶哲學隨筆意味的獨腳戲,滲混了身體/靈魂/存在的唯心論述,則教我聯想到王爾德(Oscar Wilde)的〈漁夫和他的靈魂〉(The Fisherman and his soul),漁夫愛上美人魚,但美人魚要求漁夫放逐自己的靈魂──她說,人體的影子其實並不是身體的影子,而是靈魂的影子;你背對著月亮站在海灘上,然後把你雙腳周圍的影子用刀切開,那就是你靈魂的身體,叫它離開你吧,它就會按你的話去做。漁夫照辦了,可是再無法感受美人魚的愛,而他的靈魂每年都回歸一次,勸他與它復合,但總是徒勞。王爾德說的是愛(及其失落),朗天說的是恐懼,反覆論證身體與靈魂的存在,是兩個章法迥異的文本唯一的交叉點,於是我在這一點上反覆思疑︰愛與恐懼可能源出一義,或有近親的血緣,至少是具備換喻性質的近義詞。
潘國靈的〈鴉咒〉說到一個女作家因一篇小說而身罹病劫,她的男朋友認定要「解除魔咒,我必須把這個故事寫下來」,因為劫從何處始,便從何處終。李照興的〈三世〉借攝影的殼說到相隔凡七十年的兩場瘟疫,以及宿世的愛與死。黃志輝的〈我的超文本旅行筆名〉用上八張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照片,貫串出「另一個『我』的自拍照/或光之旅程」。很奇怪,三個風格各異的故事都讓我聯想到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特別是坡的〈影子──一個寓言〉(Shadow- A Parable)︰Ye who read are still among the living; but I who write shall have long since gone my way into the region of shadows。此一寓言化的影子,除了廣義的死亡陰影,別無他物。坡的詭異故事如〈黑貓〉,也是站在生死界上展述的:明天死到臨頭了,要趁今天把這事說出來好讓靈魂安生。我曾在另一篇文章指出,幾乎所有的敘事學研究者都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對於弗氏所說的「生活僅僅是通向死亡的條條迂迴曲折的漫長道路」,他們大都深信不疑。希里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甚至在《解讀敘事》( Reading Narrative )中有此斷言︰「……所有說故事的人都是在死亡的陰影下講話。他們的敘述是與死亡達成協議的一個途徑,同時也構成驅除死亡的一個方式。」潘國靈、李照興、黃志輝的故事,都帶有極濃烈的死亡陰影,魔咒、瘟疫跟另一個「我」的光影之旅,原來都是與亡魂面對面的相濡以沫,最終無可抉擇地相忘於江湖。湯禎兆的〈湯鬼〉極有東洋怪談味,荒野溫泉的亡魂等待「替身」,倒是以死者的角度回望人跡罕至的塵世,要擺脫死亡,重返人間(回歸香港),就只有將死亡之咒施諸他者;最後勞煩「根精神」(被咒語禁錮的陽具造形神祇,要解咒回復自由,就要靠陽間的人在他的頭滴血)釋法,隱約有政治指涉,可也不必管這些,由亡魂到「根精神」,說來就是逆向的敘事精神的通幽曲徑。
羅貴祥的〈死者自由行〉和紀清豐的〈嬰魂〉都教我聯想到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當然,羅貴祥的故事中的「女學生」名叫聶小倩,大抵是有意識的誤導,然則一個在大學執教的知識分子在人散後的辦公室(書齋)對「女學生」心存異想,毋寧不脫聊齋格局。紀清豐的故事中的同性戀者在異性戀時期不知女友懷孕然後墮胎,遇見被殺害的胎兒,彷彿就是一個人經歷了前世今生。《聊齋志異》最有趣之處,大概就是本文附錄的「異史氏曰」,其中一則說:「幻由人生,此言類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動耳。」這段話不僅可以當作羅貴祥所塑造的大學教授在故事末尾反覆自我反詰的有建設性注釋,境由心生,人心所動,幻化千我萬我,對何國良那篇例外地對異靈及其感覺點到即止、甚至通篇與異靈無涉的〈有舊黑雲追殺我〉來說,也提供了一種滿有創意的讀法。要是轉換為曾譯《聊齋》的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說法,也相去未遠──比如在一篇題為〈環形劇場〉的小說,他就有此述說:「陌生人夢見自己站在一座環形劇場的中央,不論是睡是醒,這人都在思考那些幻影的答案,設法尋找一個值得活在這世界上的靈魂……使孩子永遠不知道自己是幻影,可以像別人一樣做一個完整的人……最後他才知道自己只不過是個幻影,另有他人在夢裡創造了他。」那麼,王貽興的〈上香〉儘管也沒有異靈,母親、姊姊和迪強所見所關所思所感的「父親」,何嘗不是人心所動的幻影?或者,轉換另一觀點,其後已經死去多時的母親,以及在神枱上、記憶中的父親,回望人世的迪強,對香和粥的味道會不會別有一番心事?對人世的一切又會不會別有一番「了解自己身世歷史的迫切渴望」?
十個詭異故事寫法和趣味完全不同,彷彿十方世界裡的十面埋伏,都不可避免直書/曲寫異世或異靈,那是說,都不免透過書寫,在某種意義上與死亡對話。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此早有洞悉:「死亡賦予說故事的人所講述的任何東西以神聖的特性。說故事的人的權威來自死亡。」那麼,吸引讀者閱讀小說的可能就是這麼的一種渴望︰「用讀到的死亡來溫暖自己冷得顫抖的生活。」(〈說故事的人——尼古垃.列斯科夫作品隨想錄〉)這也就是我向讀者推薦此書的終極理據。
2004.6.21
 10個男人有詭異txt,chm,pdf,epub,mobi下载
10個男人有詭異txt,chm,pdf,epub,mobi下载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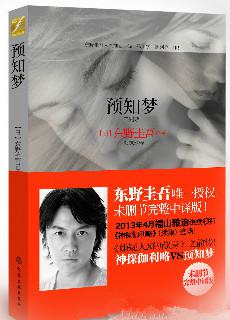
这本就又回归朴实了
可能我道行比较浅,一时半会还真的无法消化
特别喜欢作者
超赞